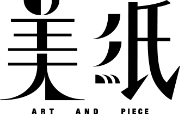一行禪師相信,走路是修行的一種,邁開步伐認識內在的佛陀,就能夠自我覺察,碰觸生命肌理。
2012年,蔡明亮開展「行者」系列,完成多部電影與展覽,當中也包括了2014年的舞台劇《玄奘》。說是一個舞台劇,但幾乎沒有任何劇情需要發生,只有兩件事:一大張白布上,穿著袈裟的李康生在夜裡躺臥著,畫家高俊宏在他身邊匍匐作畫,描繪著他的夢;到清晨,李康生慢慢站起來,在白布上緩緩走動,開展日常的修行。
TEXT yui | PHOTO OiyanChan |VENUE 大館

九九八十一難
十年的劇目,沒多大的改變,改變的只有人們頭頂的天空,以及心中的念想。《玄奘》去過世界不同的角落,但場地面貌卻大相逕庭。像首演場地布魯塞爾的停車場、維也納的舊建築倉庫、韓國光州的劇院等。「戲是一樣的,氛圍卻不一樣。」蔡明亮笑指,《西遊記》裡頭玄奘取西經有九九八十一難, 每到一個地方就遇到不同的妖怪,他們演這個《玄奘》每到一個新地方,也遇到不同的問題。
「例如第一次在布魯塞爾首演,當時我們預計會在布魯塞爾與維也納各演四場,最後全部場次都滿座了。可是李康生在布魯塞爾一下飛機就『小中風』(腦溢血),有一半的身體都沒有力氣。沒有力氣怎麼辦呢?但李康生說他要演,用他剩餘的身體去演。本來演出預定是兩個小時,是晚上八點演到十點,最後他演了三個半小時,因為實在是沒有力氣走。到十一點的時候,觀眾要趕車趕地鐵回家了,300多個觀眾走了一半的人。戲一直演,人也一直走。可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,如果你沒走,你好像就是在見證著其他的觀眾,像演員一樣,一個一個的離開。在韓國光州那次也有趣,那個場地是一個很大的studio,studio的大門打開後是一個公園,會有遊客路過。那時候我就故意把門打開,當戲在演的時候,外面的人都不知道,我就讓他們不明就裡的走進來,把他們都變成演員。」


香港的《玄奘》在大館上演,場地選址是在一個半戶外的地方。蔡明亮說:「演出的當中會有人經過,會有人停下來。沒有買票,就在旁邊(看著)可不可以呢?我覺得可以,就讓它發生,也很有意思。而且舞台靠近馬路還有汽車經過的聲音,又有酒吧的聲音,這些我都覺得很好。就讓這些現實的聲音、現實的人、現實的的狀況發生吧。」說到聲音,蔡明亮特別提到《玄奘》的配樂沒有用到任何佛教音樂,而是使用了現代的音樂,當中特別挑選了一首南音〈男燒衣〉,由杜煥演唱。

從前慢
於是這場慢的劇、放著慢的音樂,在全世界其中一個最急速的城市掀起帷幕。「我們都很怕慢。」蔡明亮笑指:「尤其是香港人吧,大家都很急,但有些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急甚麼。我的感覺是,我們在那些很忙的時間,時間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事情,而是別人要你這麼忙。所以我們根本都沒有自己的時間,很怕安靜下來,或者是很怕一個人。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年代的一種追求,但同時也是一個很致命的。到你後知後覺,想說自己到底享受了甚麼人生的時候,就只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疑問。」
「所以我覺得,尤其是我在做視覺藝術的人,是要用看的概念去啟發觀眾。然而我們常常誤解了這個『看』的內容,一個戲演完又演千篇一律,到底我們能夠得到些甚麼?其實好像沒有得到東西。戰爭的戰爭,仇恨的仇恨,富有的富有,貧窮的貧窮。像昨天我去銅鑼灣隨便走走,在時代廣場看到兩對男女在吵架。先是一位太太跟她先生在吵架,後來又有一對年輕男女在路上大聲吵起來了。我就跟我的同伴說:他們很不快樂、很『䒐䒏』。所以我常常覺得,看劇是需要時間的,很快演完一個劇的話,觀眾看到的是故事,可是看不見人。」


這也是為甚麼蔡明亮執著於形體以及行走。「所以我喜歡走得很慢。一個人的身體是很美的,一個人的身體是有侷限的。這也是為甚麼我覺得玄奘很重要,他不是一個神話人物,是真實活於歷史的人。他的存在與精神很重要,他在他的那個時代,為了要取得一個幫助人類的事物,用走路的方式,來來去去十幾年,是很辛苦的事情。我感覺到說,我們現在身處的是一個快的時代,我不能控制時代,可是可以控制我自己。我讓自己的作品比較慢一點,讓你看我的作品的時候,跟看別人的不一樣。如果十部戲中有一部是不一樣的,可能就能夠讓你有一些新的想法———原來這個世界不一定要這麼快的。又譬如說,我們以前坐飛機坐車的時候都會看看窗外看看書,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手機。但現在我們不看那些了,其實失去了蠻多生活樂趣、一些快樂的可能性。我的作品就是要給人做一點這樣的思考。」

看他走路,同時看到世界
看蔡明亮的戲劇本身也像是修行,據他的說法,就像這次大館的《玄奘》,雖然兩小時的劇目不算很長,但坐在沒有靠背的硬木椅上兩個小時;就算談不上辛苦,卻一定不會太舒適。「看我的戲不只眼睛在看而已,是身體也要有負擔的。」其實不管是舞台劇《玄奘》,在不同場合看蔡明亮許多電影作品,總是有觀眾抵不住裡頭的慢節奏與長鏡頭,開始呼呼大睡。他也坦言,自己近年想拍的大多都不是故事,像《行者》系列那樣就沒有「內容」,只是一個人在走路而已,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走路。「因為他走得慢,所以你看到他走路,同時你看到世界。」
由《青少年哪吒》到《無所住》,蔡明亮一直為作品做減法,還真的有點像一個出家人,在修行中不斷去除雜念、漸見空性。「我覺得是凸顯了那個存在的概念。倒是沒有要提防些甚麼欲念。譬如說我現在畫畫,在畫一個人,一般而言就是會畫滿這張紙。可是所做的,就是只畫那個人,不畫那個背景。所以你就你看到,白的背景、一個很突出的人,那是另一種風格。你把畫畫得很完整也是一幅畫,不完整也是一幅畫,只是要看你表現甚麼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