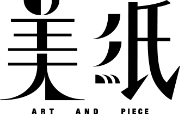本地著名舞者、編舞家梅卓燕,將於「香港藝術節」的《SOLO》,把三套早期獨舞作品——《遊園驚夢》(1986)、《獨步》(1995)、《水銀瀉》(1994)重現舞台,叫本地舞迷引頸以待。早前先睹為快,在排練室欣賞了《遊園驚夢》和《獨步》綵排,雖然沒布景沒燈光,梅卓燕只分別拿着一把金扇和一把油紙傘,躍然起舞,身段動人,已足夠賞心悅目;在扇子開合、傘子轉動之間,在順流逆流之間,如此簡約,又如此有凝聚力和感染力。
Text:黃子翔 Photo:Oiyan Chan

檢查功課
金扇與油紙傘,道具雖小,但殊不簡單,梅卓燕介紹時如數家珍,「一般扇子能打開至140度,但這把金扇,可以打開至180度,而且扇骨很密,十分扎實。」上世紀八十年代排《遊園驚夢》時,她在裕華國貨以$50購得金扇,現已漲價十倍以上,「藍田玉內向,許多事情都不說出來,總是藏在心中。」她穿著旗袍跳舞,「旗袍本身已是限制,不僅不能大動作,更像一種掙扎,在有限空間尋找表達方式,對我有很大幫助。」扇子也彷彿替她說話,開合轉撥,喜怒哀樂,「扇子是《遊園驚夢》靈魂。」
《獨步》的道具,則是油紙傘,「很多細節是人手入榫,很骨子,在燈光照射下特別漂亮。」《獨步》最早於1995年演出,當時油紙傘跟金扇一樣於國貨公司有售,僅$25一把,蘇杭街一帶藤器店也能找到,但現已絕跡本地,她只能通過網購從內地進貨,然而也升價十倍,「因為工序繁複但利潤不高,要到湖南等地,才有師傅製作。」
早前「香港藝術節」找她做演出,她本來想發表新作,但他們卻想她跳最早期的獨舞作品,她當時笑着回應:「要檢查功課嗎?」又怕門票賣不出,但結果早早售罄。當年創作,怎麼料到,三、四十年後仍然要跳?身體是否能跳是一件事,作品有沒有過時是另一件事,「會不會看起來就像穿錯了衣服?」但她決定不作修改,徹徹底底原汁原味,「當時怎樣跳,現在就怎樣跳。其實是一種檢視。」

可以是她 也可以是自己
創作於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的《遊園驚夢》、《獨步》、《水銀瀉》,多年來均有重演,其中以《遊園驚夢》演出次數最多。《遊園驚夢》是梅卓燕第一支被委約的獨舞作品,1985年,她參加市政局舉辦的「香港青年編舞大賽」,贏得中國舞組冠軍後,拿着一萬元獎金,首次赴紐約學習當代舞,衝擊不少,帶來很多反省和探索,關於舞蹈、身體表達,以至東方和西方的美學,「中國舞可以這樣跳嗎?那些材料,怎樣跟今天連繫?能否再有表達性?」
翌年曹誠淵為香港舞蹈團統籌表演項目「文學與舞蹈」,問她有沒有興趣編舞,她立即想到白先勇的《遊園驚夢》,又表示對小說中塑造的藍田玉形象、表達一個女人的一生遭遇,還有意識流的手法、崑曲的氛圍,印象深刻,「編舞一定要找到一個手段。這個文學作品與舞蹈之間,有太多連結。」

譬如主角藍田玉是一個唱崑曲的女子,有很多關於身段的東西,這跟中國舞的身段是一樣的。還有小說描寫,一個女人坐在舊屋裏,於一抹斜陽下撥扇,而中國舞、民間舞就有很多扇子的運用,「戲曲《貴妃醉酒》那把金扇,就是我在《遊園驚夢》拿着的扇子。」或許也勾起她小時候太婆帶她看戲曲的憶記?事實上,她正正因為恨穿戲服愛戴頭飾,才去跳中國舞,「潛意識一定有吧。」
於是她交出改編之作,「也斯取笑我,二十多歲女生,懂不懂《遊園驚夢》寫甚麼?」但《遊園驚夢》演出後,觀眾反應很好,舞評亦佳,證明演繹到位,然而她還是謙遜地說:「文學與舞蹈跨界演出,在八十年代是新鮮事,大家也可能覺得我年輕,敢做一套經典作品,是有加分的,不盡然是我的實力。大家都很疼我。」她也以較抽象的方法演繹,「沒有破壞讀者對原著的想像。」

《遊園驚夢》一直以來受到各地舞界歡迎,演出不斷,那麼多年來,她沒有改動任何一個舞步,「但怎樣表達、怎樣拿揑,完全不同。但我是不自覺的。」她笑說,跳獨舞有個好處,每次再跳,就像穿上一套舊戲服,「作品就在我的身體裏。」早年跳《遊園驚夢》,她較投入到故事世界裏,怎樣演繹角色,怎樣呼應文本,「但後來再跳,我漸漸忘了故事。我可以是她,也可以是我自己,甚至是任何一位女性。」舞台上放着兩張凳,「我坐在其中一張,另一張沒人坐,任你想像,那可能是一個男人,或是一種身分的對調。」還有一面鏡,「一個人正在面對自己?或看到以前的自己?」
跟傘子和風對話
《遊園驚夢》是她的當代舞初嘗試,後來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,再次赴美習舞,追溯後現代舞蹈(Postmodern Dance),「我當時很專注地學習Contact Improvisation(接觸即興)的技術,從兩個身體開始,通過重量及重心轉換,尋找各種反應,是一個溝通的關係。」她覺得「接觸即興」最厲害的是包容性,讓舞者反省自己的文化、舞蹈背景,然後找出特別之處,「沒有排他,而是收納,突出每一個特性。」她想到中國舞有很多道具運用,好像手巾舞、扇舞、劍舞、水袖舞,都跟物件有關,「能否把『接觸即興』加進來?」

1995年由CCDC委約的《獨步》,是她第二份「功課」,既是獨舞,也是她跟傘子和風的對話。被問到創作緣起,她提到一個念念不忘的情景,「CCDC黃大仙舊址,外面有條『長命斜』,每次下雨,有人舉傘瑟縮一角,有時是兩個人在一把傘子下擁成一團,我總是被這個畫面震撼。」加上當時的社會氣氛,大家面對去或留的疑惑,「我突然想到,在橫風橫雨之際,一把傘,就是容身之所。」

於是她決定跳傘子舞,然後每天都跟它「玩」——打橫,可以開傘;打直,可以開傘,「也可以利用風去開傘。」當傘子在動,便掀起了風,她一直閱讀風向,與風對話,「尋找風和身體之間的關係。」演出時,也會灑下紙屑,傘子在轉,紙碎也跟着轉動,「我跳舞時感覺到風,觀眾卻看不到,但有了紙碎,大家就看到風的流動。」風視覺化了。
像鏡石閃閃生光
至於1994年的《水銀瀉》,由「香港藝術節」和「比利時國際藝術節」聯合委約。舞台上有一個八呎乘八呎的鏡台,看起來就像一個水窪,上方掛着五塊錫紙,形成「水銀瀉下」的美妙情景。她笑說,最初想到用錫紙,是因為一次煮食時,用錫紙包裹食物,覺得有趣,興之所至,翌天便跑到超級市場買了幾卷錫紙,回到Studio,把錫紙鋪在地上,像小孩一樣站在上面玩,「用腳揑它,成了一塊,感覺就像雕塑,玩得很開心!」

雖然好玩,但怎樣發展下去,她苦無頭緒,唯有請教資深劇場工作者何應豐:「何爺,我弄了一些東西,很想發展成舞蹈,但不知道該怎樣做,有沒有興趣來看看?」何應豐便來到她的Studio,看她玩錫紙,然後想了一整天,告訴她,讓她在一個八呎乘八呎的鏡台上跳舞,然後錫紙從上方吊下來,「我一聽到立即『毛管戙』!」演出時,她把玩錫紙,弄出各種形狀和聲音,加上一盞拍戲用的大射燈,「我就像鑽石一樣閃閃生光。」她笑說,這個作品很有畫面感,抽象但強烈。

《水銀瀉》於1994年在「香港藝術節」首演,然後到比利時演出,接着於法國、葡萄牙等地巡迴,一直在歐洲得到表演機會,「1990年到2000年,是歐洲市場養活我。那個年代,香港較少獨舞作品,獨立舞者在香港根本拿不到資助,很難在港發表作品。」她帶着《遊園驚夢》、《獨步》、《水銀瀉》,踏上歐洲巡演之旅,1998年,更獲德國著名編舞家翩娜包殊(Pina Bausch)之邀,在她的烏珀塔爾舞蹈劇場(Tanztheater Wuppertal)二十五周年,演出《遊園驚夢》和《獨步》,演出後,全場起立。
「後來翩娜問我,想不想把《獨步》編成群舞?」她當然說好,於是在2000年替Folkwang Tanzstudio,編了一個以《獨步》為基礎的足本作品,以「四季」為題材,灑落不同顏色的紙屑,象徵不同季節綻放的花;既然是群舞,傘子也不只一把了,有長傘也有縮骨遮;自動傘更有機關感、力量感,有時紙屑落在傘子上,「砰」的一聲打開,紙屑立即飛彈,「有放煙花的感覺!」

九十歲跳更好
今年六十六歲的梅卓燕,堅持每天做一小時伸展、一小時身體練習,即使沒有演出,也日日如是,已成習慣,「身體是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的唯一載體,沒有身體,甚麼都做不到,需要好好保養,特別是舞者。」喜歡下廚的她,坦言煮食過程很療癒,也跟編舞、創作一樣,怎樣選材,怎樣碰撞味道,怎樣擺盤,給甚麼人做甚麼菜,她都覺得很有樂趣,而吃一頓飯,就像跟身體對話,「哪天精力不足,吃些黑色食物吧,不同顏色食物,對應五臟六腑。」

她不諱言,現在身體狀況很好,即將演出《SOLO》,最常重演的《遊園驚夢》,當然最有信心,甚至覺得九十歲去跳可能更好,但《獨步》頗考驗體力,她形容為「上山落地」,跳上跳下跳來跳去,對膝頭關節負荷很大,甚是挑戰,為了演出,她準備良久,收拾身體,「跳一次少一次。」至於《水銀瀉》,她覺得沒有年齡限制,何時跳都可以,空間最大,「是當下那刻跟物件的呼應,怎樣玩都可以。」
梅卓燕《SOLO》
日期:3月27日至29日/8:15pm
3月30日/3:00pm
地點: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網頁:www.hk.artsfestival.org
圖片說明:
1/梅卓燕將把三套早期獨舞作品——《遊園驚夢》、《獨步》、《水銀瀉》重現舞台。
2至5/《遊園驚夢》是梅卓燕第一支被委約的獨舞作品,一直以來受到各地舞界歡迎,演出不斷。(綵排圖片)
6、7/梅卓燕堅持每天做一小時伸展、一小時身體練習,坦言身體狀況很好。
8至11/《獨步》是梅卓燕跟傘子和風的對話,她一直閱讀風向,尋找風和身體之間的關係。(綵排圖片)
12/雖然不改舞步,但怎樣表達、怎樣拿揑,完全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