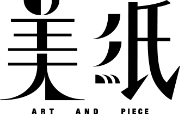《親陌》(Close)是去年第75屆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得主,比利時導演魯卡斯當(Lukas Dhont)繼4年前首作《夢女芭蕾》(Girl)後,再次將視點放到年輕的男孩身上,刻畫出焦躁不安又敏感的青少年成長時期,上次男孩決定變性作女孩,今次卻是13歲男孩本來友誼深厚,卻因為同學的閒言閒語而逐漸疏遠,最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《親陌》入圍今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,導演提到他希望拍電影讓更多人認識事實,帶出這一場男孩們認識自己、對抗世界的內心鬥爭,又認為年輕人比成年人更聰明、更真心。


《親陌》(Close)與《夢女芭蕾》(Girl)都是關於青少年的故事。為何想拍攝電影聚焦於13歲至15歲的成長故事?
我希望展示一個年輕人的世界觀。每個人年輕時,都是第一次去認識世上眾多事情,包括了解我們自己,所以在眾多可能性之間,會開始出現一個發生對抗的時刻。慢慢了解到,其實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標籤、規範、期望等的社會。至少自出生以來,身體已經為我們設下了這套規則。
在這套規則下,我年輕時感到非常困擾,經常感到自己無法達到別人對於「男性」這個期望,所以我從來沒有真正認同自己,也找不到其他獲得共鳴的例子。 因此,在我年輕的一段長時間裡,我想拍電影,因為可以逃避現實。後來進入電影學校及踏入成年後,我意識到拍電影更能面對這個現實,讓人更了解世界上有更多的年輕同性戀者。

《夢女芭蕾》談及身體及外表,《親陌》則關注更多精神方面和心理視角。為何你對在這兩部電影中有這個轉變及探討?
我認為,這兩部電影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關於身體的。《夢女芭蕾》是一部真正關注與身體關係的電影,片中這個年輕人如何開始理解她的身體,她卻不是世界上一般人所認為的「女性身體」。
至於《親陌》,我認為有更多探討行為及行為方式,包括在團隊中的行為。片中兩個主角在一起,直到世界要將他們分開,二人站在分岔口上,迫使他們走向不同的方向,從而觸痛變成了摩擦,摩擦變成了鬥爭。對我來說,《親陌》是一場關於內心的戰爭,一場心理健康的鬥爭,當中包括了身體,也有悲傷和內疚。雖然身體與內心好像是分開,但它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繫。


這兩部電影特別用上芭蕾舞及冰上曲棍球,正是你眼中最代表女性及男性的運動?
電影所呈現的確實如此,但除此以外,這代表一種刻板印象的暴力。當我們談論芭蕾舞時,它是女性優雅經典形象的最高形式;然後我們談到了冰球,這項運動卻是殘酷和暴力的。當《親陌》的男孩穿上這件盔甲並成為冰球員時,那些形象卻消失了,可見這是一種明顯的視覺語言。
片中有個相似的畫面,一大群黑鳥都在天空中朝著同一個方向飛翔,這個畫面既美麗又令人痛心,非常代表著我們年輕時的想法。我們當中的不少人都希望自己屬於大多數,所以我們朝著其他人的飛翔方向而飛去,但一心只是想成為他們的一部分,卻沒有想到自己真實的想法。對我來說,那些打冰球的男孩,穿著黑色盔甲的男孩,確實與那些黑鳥有點相似。

這兩部電影的角色都比較開放,尤其是角色的父母。在你眼中,電影中的父母角色的象徵意義是甚麼?
相信大家都明白,這些關係非常複雜。很多父母經常被描述為不理解孩子的人,但我對這方面興趣不大,我更想談論社會之間衝突,以及一個所有人都被分配角色的世界,因為這才是衝突的真正根源。我覺得可以將父母視為主角,或是有缺陷的人,但他們竭盡全力並盡力為他們的孩子服務,這才是我最感興趣的事情。我確實認為這兩部電影中都有探討這方面的溝通,源於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刺激心靈的世界,希望大家能夠學會心靈方面的互相溝通。


找年輕人做主角實在不容易,你認為他們夠成熟地了解這部電影的訊息?
成年人經常低估年輕人的想法。我總是盡可能與他們的視覺保持平衡地出發。同時,我覺得他們的說話非常聰明,甚至經常覺得他們比成年人更聰明,特別在情感之上,因為他們比較真心,以最純粹、最本質、最激進的方式說話。
有時成年人會審查自己,或者說一些預期別人會接受的說話。但很多方面,年輕人都只會說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一句,所以當他們閱讀劇本時,我認為他們對劇本很有想法,並以很好的方式討論劇本,最後亦因為那次談話,重塑了我這部電影變成更真實的樣子。

最後,不少影評人都說你的電影風格和戴丹兄弟(Dardenne brothers)相似,那你怎麼看呢?
戴丹兄弟?這真是一個很好的恭維,感覺良好,真的。戴丹兄弟來自比利時,我一直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是,他們真的與角色處於同一視角出發,這是我一直努力做到的事情,而且他們在工作中有很強的節奏,隨著世界各地的進步,我真的認為在我們在電影語言中進步。
戴丹兄弟對真實事情非常感興趣,他們有一種非常準確的現實主義,但我認為自己的電影在視覺風格上,更喜歡使用色彩和表現主義,以非常有風格的方式去呈現真實,但當中亦有部分元素,提醒觀眾這是虛構的,所以兩者有點不同。不過,我當然會接受這方面讚美,因為他們的確在我的電影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