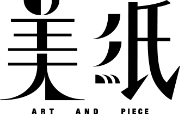早幾年的江記(江康泉),正忙於將屈原生前故事大反轉,推出本土動畫《 離騷幻覺 Dragon’s Delusion 》眾籌計劃;三年後,《離騷》已然成為一個香港品牌,大膽推敲著賽博龐克美學(cyberpunk)風格,更延伸出個展「江記的戰國龐克」,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出。
如今展覽即將回流香港,將大館變成連接過去和未來的賽博龐克宇宙,江記也親述了自己的意圖:「很多時候我們對作品本身是不認識的,都是初接觸後才反過來了解,所以屈原是甚麼?每個人進入故事的方式都不同,更不用怕藝術有很多符號上的東西別人會不明白。」幾個時空交錯碰撞,江記的屈原,既是漫畫,也是映畫,也是一個冥想的過程:假如詩人屈原在死後的二千年後再度復活,由楚江一下子被投擲到賽博龐克的未來之中?
這樣一個穿越戰國與舊香港時空的故事,在演化成海外展覽後,堆疊了許多為人熟悉的香港視覺元素,廣告牌、天橋、鐵皮排檔、霓虹招牌應有盡有,更是由巨型屏幕和霓虹裝置組成的沉浸式體驗。到底由《離騷幻覺》為主軸發展出來的「戰國龐克」,它將會帶領觀眾的精神到何處?在感受「紙紮色衝擊」前,不妨先聽聽他本人說法。
TEXT LEON
INTERVIEW YUI
PHOTO COURTESY OF 大館


「江記的戰國龐克」來到大館,有甚麼定位與特質?
它原本第一站就是去年11月在美國三藩市的Asian Art Museum。至於主題,通常提起想像科幻的世界,往往都是關於未來的,但這個展覽叫作「戰國龐克」,而我選擇切入的角度,則是用歷史去感悟人和科技的慾望。因為科技其實是和慾望有關,很多科幻故事都是在說人類如何用科技去滿足己慾,今天可能說的是AI、納米科技與神經科學,以前的人則是鑄青銅器、擴張軍力或者秦始皇煉丹,那麼過了幾千年,他怎樣利用這個技術呢?背後的元素好像值得說下去。
所以,是次展覽其實就是重步中搭建一個平台,讓現在和過去開始一場說話,尤其美國那邊有很多藏品,其中有一些青銅器,當時我便將展場上的光作為它們與我影片溝通的渠道;如今來到大館策略就有不同了,大館作為歷史建築物,本身就是我要對話的對象,所以我們有一段新影片去它交流,包括去年到現在的發展脈絡。


談到這點,既然展覽由《離騷幻覺》發展出來,它將會帶領觀眾的精神到何處?創作背後有甚麼意圖?
如果單說這個新作品,本身它是有很多很強烈的香港元素在裡頭,但去到外面演繹時我們沒有很專注於這些符號之上,因為出奇地觀眾們都很有冒險精神,他們會先被表現的手法,如光影、顏色、氣氛所吸引,繼而才追問屈原是誰?變相是進入世界之後再去找尋意義,我想這也是大家欣賞藝術的一個過程。
很多時候,我們對於藝術的認識都是後知後覺的。所以當展覽來到香港,更加要降低那種令人疲憊的香港元素,尤其大館這地方已經足夠多光影,因此「符號」相關的東西,我這次選擇更抽象地去捉緊情緒。我從聖法蘭西斯哥很多不同族裔朋友身上看到,他們原來有很多新一代和自己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隔離,這種離散的情緒其實是種意外收穫,讓我發現其實香港近幾年的經歷是世界性的,很多地方和我們正在經歷同樣事情,而我們確實可以有更大的連結去面對離散。
所以這次新作品《流血,流淚,流浪》,就是用三個窗作螢幕,好像玻璃畫的概念去延伸成動畫,呈現出如置身教堂的感覺,讓觀眾靜下來沉思面前看似分開的故事,其實它們都是互相扣連著;希望可以說中大家當刻的情緒,有一個交流的機會。
你曾提及,屈原是個頗特別的人物,他被塑造成愛國人物,但死因決非那樣淺薄。你如何去理解他這個人?
我認為在我們的教育中,對於屈原的理解,或者他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個愛國詩人,這般理解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去追尋。然而,如果從現代心理健康的角度去看,其實很多創作人或者有情緒問題的人都是這樣,平時看他可能很開心,但情緒其實很兩極。再看回屈原,他的作品色彩繽紛,像是生命充滿了熱情能量,但你想像不到有這麼強的能量的人會去了結自己的生命,所以相比我們認識的他,我想屈原本人要複雜很多,也就令我筆下的他時而幽默,又時而隱藏著一股壓力似的。屈原的可塑性,就在於他處於那個時代,其展露出來面向大眾的面貌,跟我們小時候想像之間的距離。
另外,開始寫他時也有一段趣事。在我剛剛三十多歲那會,已經有種感覺這個城市和我距離很遠。無論原因是什麼都好,我想每個人和過去都總有著一個哀愁的連結,因為你永遠回不到這個過去。我就開始覺得創作這個角色,需要有一個共鳴點或是從他身上找尋一個出口,去探討人是怎樣消化這些情緒,繼而有一個情緒上的寄託可以安放,才慢慢地發展出一個叫做阿祖的角色,是屈原的複製人。如果阿祖繼承了他的想法,繼承了他的歷史,那麼這個機械人會不會有新出路呢?還是他會回頭……這種宿命的命題是《離騷》很重要的骨幹,我就是透過寫故事,不停思考究竟這樣行不行。


如何看待Cyborg?
我覺得這個問題變得很迫切。Cyborg,這個問題就是「人」的定義是甚麼。隨著AI發展,以前可能只是純粹哲學或者宗教性討論,但將來可能就要決定它有沒有合法的地位,又需不需要負上一些人類該負的責任。所以我們要回過頭去定義「意識」,這些討論我覺得很多作品都有涉獵到,譬如《攻殼機動隊》最後結尾,就是資訊的海洋本身就是一個有自主意識的生命體。我覺得這是很佛教的想法,就像討論「時間」一樣,現實其實是沒有時間的,你只能量度到那顆原子。那麼「意識」或許亦如是,可能是沒有意識這回事,你只能夠知道它資訊交流的程度有多複雜,當那個物體有很大量資訊交流時,它就會表現得好像有一個自我意識在那裡,我想我的看法傾向這方向多一點,整個宇宙都有它的意識存在,只在乎你的切入與聯繫方式。

延續Cyberpunk「 High tech Low life 」的討論,現代香港已經逼近這種狀態,你同意嗎?
「 High tech Low life 」,其實從來都是可能的。幾百年前有人識字,有人不識字。已經是這情況,有些人掌握不到資源,而Cyberpunk則是集中科技上的資源。例如看《Ready Player One》,有沒有錢購買裝備,都是一種貧富懸殊的表現。香港,絕對是其中一個高科技,低生活的城市,深水埗就是完全體現到這差距和呈現的方式;但我覺得香港不只是這樣,例如重慶大廈,有很多非洲人來買舊東西寄回鄉下,這又是另一種高科技呈現。
我認為「香港」這片土地,絕對是「賽博龐克」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創作標誌。這當然牽連到歷史發展的背景,例如《Blade Runner》等很多作品,都會把這裡塑做成「無政府狀態」,我覺得我的作品很受這種想法影響,但香港的矛盾性更是出乎意料。因為國外電影會把香港描述得沒有自然環境存在,但你在這裡生活,你便會知道這裡是與自然混在一起的,明明半小時車程可以去行山潛水,也可以坐半小時車變成深水埗,這些在別的作品中都沒能體現出來。
於是《離騷幻覺》我很刻意地講了山和水,雖然是科技主題,但其實香港最有特色之處反而是如何把它們強行連接在一起,這才是最「香港」的地方。所以今次其中一個作品也是用霓虹燈做了山和海的手勢,因為人和自然觀感上的關係,不過是觀點與角度的比較:我們的生命很短暫,所以你覺得山是不動的,但其實山也會偏移。最終,這些想法啟發了我去講述關於時間、科技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