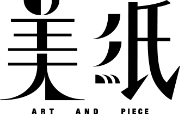對綠葉劇團藝術總監黃俊達來說,《山海經》當然是一部結合神話、遊記、巫書、志怪小說的奇書,甚至以「地理書」理解也無不可,也愈讀愈科幻,「時間是否不存在?」他以《山海經》取經,譜出狂想曲,去年以《山海經》第一部曲──《山川命》,作階段展演,今年9月上演《山海經》第一部曲──《山川命・終章》,召集跨文化、跨地域的演員陣容,以他最擅長的形體語言,結合戲曲、梵音、能劇等不同元素,築起一個不知何年何月何時何地、充滿儀式感和視覺效果的奇幻之境。戲還未演,他已有直覺,做出了最滿意之作。
文:黃子翔 攝:Oiyan Chan 圖:西九文化區、綠葉劇團


天地之間
約二十年前,阿達在書店看到《山海經》,一時好奇,買來看看,雖然讀不太懂,但被那些奇奇怪怪的圖畫吸引,就當成「公仔書」好了,「有的有幾個頭、幾隻手,有的只得半邊身體,到底是甚麼來的?」獵奇過後,他一直把書束之高閣,直到四十歲,他忽然心血來潮,重讀《山海經》,多了不同感受,「人跟怪獸,好像沒有分別?」也跟宗教、道家有關,「道家講隨性、跟自然連繫。如果你不去想自然,只想自己,便會失衡。」他覺得《山海經》有一種開放性,「你想怎樣看就怎麼看。」

阿達最初跟負責《山川命》故事、文本創作的米哈,談到要做甚麼演出時,二人不約而同想起《山海經》,「我跟他都離不開經典,經典實在有太多東西可以做,還有很多事情未被發掘。」創作醞釀五年之久,因為疫情等各種原因,一直延遲,直至去年演出《山川命》,今年9月再來《山川命・終章》。《山海經》有段文字:「命山川,類草木,別水土」,他想到,如果把動詞變為名詞,「山川命」,又如何?「既可獨立地看,也可以連起來讀。」就是磁場效應,如果人類有執念、負面能量,天地之間也感應得到,「愈多人禍,愈多地震、天災。」

演員是一面鏡
《山川命》去年上演,演出結束,不設謝幕,主演韓梅席地而坐,台上只剩下一束火光,「有些觀眾坐了很久,看着火光,看着阿梅,不願離開。也有觀眾離場時,向阿梅鞠躬。」有些觀眾看到阿達,向他合手,用身體說多謝,「氣場很有趣,觀眾看後,不知要說甚麼,又不肯走。」有的分享時娓娓道來,彷彿比他們更清楚箇中故事;有的很感動,得到很大啟發,似乎很久沒被那麼強烈的張力濃罩,「有一種儀式感。」
上回講到,帝堯之子丹朱,發現山神已離去,決心救回死山;到了《山川命・終章》,丹朱帶着《山海經》上山下海,途中得妖獸襄助,卻誤釋封印、喚醒惡神,並捲入巫師們的陰謀。訪問那天,走進排練室,看了其中一幕:眾人遇上鬼疫,惡獸窮奇路經此地,把眾人救回;少女一眼不眨,流下淚水,十分懾人,「演員是一面鏡,你會看到真正的你。」

跨文化跨地理
《山川命・終章》從《山川命》的五位演員,增至十多人,當中有來自內地、日本、印度、非洲、意大利的表演者,帶來粵語、普通話、中國方言、英語、意大利語、馬拉雅蘭語、梵語演出。阿達覺得,這個故事需要有聯合國一般的陣容,就像《山海經》的拼圖;不同的語言特性,可能源於某種怪獸的特徵,令人有不同聯想,「對我來說,人的善惡、上山的慾望,以至怪獸與人之間的關係,是一種跨文化、跨地理的東西,需要有這種選材。」


那位印度演員,本身學習梵劇,「他跟我們閱讀怪獸,很不一樣。」飾演刑天的日本演員,是一位劍士,會在寺廟做一些儀式,這次演出,他會舞火劍,「最後那座山,變成火山,被激活了。」喜歡戲曲的阿達,讓演出結合戲曲、梵音、能劇,還有念誦(Chanting),「基本上所有唱詞、戲曲,都由祭祀開始。」人生也如儀式,「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這個『祭祀儀式』,你準備好了嗎?你怎樣迎接這一刻?」


阿達坦言,《山川命・終章》是迄今最滿意之作,「好像不需要用過去那種力量去排練,也因為人多了,磁場不同。大家很有心,促成一件事,很夢幻!」他的《山海經》故事,還沒說完,既然事先張揚是第一部曲,接下來還有其他章節,從人間,到妖獸,到天地,「這個年紀,似乎是時候去做『部曲』。」那些或是另一種演出形式,可能是沒有語言的舞蹈劇場,可能是一個純粹的舞台美學空間,「看不到人,但空間在動。」最後目標,是促成一個系列,「六小時的戲,一天看完!」

西九文化區 x 綠葉劇團
《山海經》第一部曲──《山川命・終章》
日期:9月7日至9月14日
地點: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
地點:www.westk.hk/tc/event/book-mountains-seas-finale
(節目由西九文化區與綠葉劇團聯合主辦及製作,為西九創作人系列節目之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