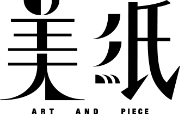陶瓷創作愈來愈受歡迎,不少人喜歡尋求內心平靜,創作後又能與製成品打卡。不過,藝術工作者列宛旻(Xapa)對陶瓷卻有進一步的想法,不只是潮流興趣,她更喜愛透過陶瓷說故事,從中思考物料的重要及變化。
早於學生時期,Xapa曾經參加過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校園藝術大使計劃,接觸到不同形式及範圍的藝術,從戲劇演出到陶瓷創作,她一直思考陶瓷對自己的影響,因一次機緣巧合下,更成為了首位在香港實行「棄陶重生」的人,鼓勵陶瓷回收,希望令不再被需要的陶瓷,轉變成有用的物料,又嘗試將它化身成為珊瑚石保育海洋,即使面對重重困難,她依然堅持下去。
Text: Nic Wong|Photo: Oiyan Chan|Special Thanks: 香港藝術發展局

為何當初會選擇陶瓷作為創作媒介?
小時候我一直玩戲劇,每年暑假都有玩,中學時轉到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時候,陶瓷是其中一項選修科,就重新開始研究陶瓷。以前玩過一個暑假,即是參加那些興趣班,跟著玩完又停過,再在書院時重新接觸。後來我在香港浸會大學接觸了很多不同的素材媒介,包括木工、金屬、玻璃等,尤其金屬和玻璃,都是三秒之間要做的決定,但我每做一件事,可能都要做很多事前規劃,或者雕琢了一些東西,所以眾多素材之中,覺得陶瓷和戲劇很相似,所以我繼續做下去。
演戲方面,我們要排了很多次,才給觀眾看,即使觀眾來兩、三場,他們看到的那一晚,我是不可以複製到第二天,這方面跟陶瓷哪個位置很相似;陶瓷的話,我可以將東西放進密實盒或膠袋放得很久,之後我才拿去燒。當我拿去燒製的那一刻的,那一刻就是定型了,就像出來表演一樣,它不能逆轉,不能重新再來一次,所有東西都固定了。

現在你的藝術家狀態是全職、半職還是自由創作?
一半吧,可能有一半時間都用來做陶瓷,事實上每天我都花一半時間做陶瓷相關的東西,而正職的文職工作上,亦有一小部分與陶瓷創作這件事有關。坦白說,我知道自己不只喜歡一個媒介,正如當初我在演藝學院讀書的時候,已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學的狀態很不一樣。同學們總是心想自己只能夠演戲,不演戲的話,將來沒有生活、沒有前路,演戲就是唯一。我卻覺得世界很大,可否嘗試其他東西?我很喜歡演戲,但生命不能夠只有它,不想好像上班一樣,所以我經常有種跳出圈圈的感覺。很多時候做演員,就成為了導演的工具,要接受對方的意見,走上對方想走的路,正好我遇上陶瓷,這是一個好的比喻,由自己出發,任由自己發揮。

很多人用陶瓷創作,你更進一步從事「棄陶重生」,當初是如何接觸到陶瓷回收?
記得在書院讀書的時候,有位老師跟我們說,做陶瓷要想清楚一下究竟應不應該燒,因為陶瓷沒有丟棄的途徑,亦沒有回收的渠道,那時直接影響了我對於陶瓷的想法。直到讀香港藝術學院時,又有老師跟我們說,陶瓷是可以回收的,香港沒有人做,誰人做了就會發達的,現在我做了,完全不是那回事(笑)。當時他提及回收那件事,在我心裡撒下了種子,後來我去了德國做交換生,機緣巧合地觀摩到外國回收廠的項目,發現陶瓷真的可以重回變成一些粉狀,原來真的有得做。後來回港後獲得一些創業,資金發展這方面,我便努力嘗試。

為何想專注下去做「棄陶重生」?
我覺得香港人看不到物料的重要性。每每我去教班,不少人沒思考到陶瓷應不應該燒製,又認為陶瓷反正可以回收,有理無理就燒了,又有人認為自己花了錢參加興趣班,想將陶瓷弄成怎麼樣都沒所謂,但我認為對待陶瓷不應有這方面的消費心態,很想教育一下大眾:其實陶瓷是非常從物料出發的,到底這個泥夠不夠黏,或是為何會有這種顏色?很多東西都能解釋到,我就想在這些位置,不停在工作坊講解這件事。


持續參與推廣回收這件事,是否真的很大挑戰?
老實說,我在香港可接觸到機器有限,很多時候都只有我一個人,我不會開車,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,或者推著車子。我也不想這樣說,但我是一個女生,力量始終有限,就算多大力,可能最多只能搬到15公斤,變相一次過不能搬很多東西,很需要別人幫忙,感到很不好意思。同時,不少人認為既然可以回收,就有一種做更多也沒壞的狀態,的確很難改變大家的想法,但如果大家試試如何著手回收,感受一下搥石仔的困難,就知道這是真的辛苦,才不會如此燒完後隨便丟棄,明白到陶瓷回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現在你花很多時間投放於不同範疇,除了日常文職工作外,關於陶瓷的包括回收、實驗、教育等,會否少了很多時間去創作?
的確,現在我很少時間做創作。我從事創作的狀態,通常都是有展覽就會開始,再計劃怎樣做,所以近來的確少了這樣做,但一旦我突然收到邀請,當然會調整時間的比例。相對上,現在自己的藝術事業可能算是停滯了,好像是休眠期那樣,身邊有很多同學都有在畫廊開始舉行展覽,自己未有機會的時候,怎樣都會有失落,但我覺得還好,總有這些時候要等待一下,就先做其他事情吧。

你現在眼前的目標是怎樣?
陶瓷回收方面,我養了幾塊珊瑚石,利用陶瓷回收的物料,製作一些放在鹹水缸裡養活,這算是試驗階段。那些項目不是產品,算是一個研究的結果,因為我想研究能否提供足夠營養給珊瑚。我還在嘗試將這些回收物料,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物料,混合陶泥等, 看看它會變成甚麼效果,怎樣令它可以生長得好一點。我比較享受實驗中的事,喜歡自己的時間去看事情發生成怎樣,也是我比較開心的狀態。另外,我很希望香港有收集店可做到陶瓷回收,很多人經常問我:「可以在哪裡拿陶瓷給你?」如果有些店舖可以幫忙,那大家就可更容易地接觸到回收這件事。


早前你在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校園藝術大使計劃中分享,呼籲年輕人努力參加不同活動,嘗試找出自己的路向,再找一個屬於自己的舒適圈。現在的你又建立了舒適圈沒有?希望跳出舒適圈嘛?
我的舒適圈應該是,在沒有人找到我的情況之下,亦即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,那樣我就可以安靜下來創作。身在香港,卻很容易被人找到,當朋友知道我在香港,就會找到我,但我在外國的時候,雖然都有些朋友,但不會是香港那樣親近的,反而我會再冷靜一點,對我創作的狀態來說,是最舒服的。現在身邊經常發生很多很繁瑣的事情,可能我一下樓梯,走一條五分鐘的路,已是人來人往,很多事情令我感到很急促,舒適圈變得很小了。
現在我很清晰自己究竟要甚麼,需要甚麼,不需要甚麼。我希望做陶瓷,這件事比較順利,但我又希望可以令更多人認識陶瓷回收,讓我可以去其他地方閉關兩個月創作,然後回來,我希望是這樣的狀態,但始終是創業,我明白有很多東西都確實被現實限制了。

你認為最需要甚麼方面的協助?
香港很少人做棄陶重生,最重要還是要透過一些儀器將陶瓷粉碎變成有用的瓷粉,但那些裝備並不便宜,我亦很擔心電壓及安全問題,因此只能購買來自歐美最先進的儀器,相對上成本及運輸費用很高;加上我現時的地方不大,始終不是工廠環境,只能夠用某些東西大小的儀器,不能夠大過某個長度或闊度。最近我也嘗試找其他工作的地方,但租金實在太貴,沒辦法了。

最後,作為藝術家的你,覺得眼中的美是甚麼?
我接觸最多的是物料,它未必是一種很傳統眼光的美,但我喜歡從日常生活中觀察入微,能夠察覺到一些很小的事,已經是眼中的微,即使它可能是跌在地上的一部爛電話,可能它依然在響起,我也會錄下它的聲音。我覺得這些東西,就是能夠做到那種觀察入微的狀態,其實這已經是很美了。